(通讯员:胡志康)2020年12月26日—12月2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三届年会暨“人民:概念与历史”线上学术研讨会。会上,与会学者们重新回顾了“人民”的概念与历史,从“象征性代表”、“人民战争”、“中西比较”、“向下超越”、“人民的两个身体”等入口多角度地切入“何为‘人民’?‘人民’何为?”这个历史性问题,以图重新发掘20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经验。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绍光教授做了题为《“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的演讲,并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刘晨光副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涛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展开讨论。
王绍光老师从“象征性代表”切入,指出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对“意符”(ideographs)也就是意识形态符号的塑造。他认为象征性“意符”具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性,至少包括“承诺—责任”、“认同—团结”、“倡导—促进”与“赋能—增势”四种功能。任何政治体系都需要配套的“意符”系统,而“人民”、“为人民”、“人民共和国”在当代中国的符号与话语(意符)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通过系统的概念史梳理,王绍光老师指出,今天使用的“人民”概念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及其第一代领导人。创造“人民”的过程也是认同人民、解放人民、代表人民的过程。从甲骨文、金文资料与前人研究出发,可以发现“人”、“民”二字在古代中国的两种组合“民人”与“人民”,都是指社会底层民众,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不带贬义的“人民”一词。不过,即使在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那里,“人民”还是常常和“国民”、“公民”等词混用。自中共成立直至1934年间,在其“意符”谱系当中,“阶级”、“国民”与“人民”三词存在动态的升降变化。1935年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概念的适用性出现根本的转折。在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人民”一词出现57次,超过此前7年频次的综合。随后,《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明确了“人民”的概念框架,其核心内涵为“革命的动力”,否则便在人民之外,外延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主体是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们是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超过百分之九十。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概念的包容性与代表性。瓦窑堡会议不仅回答了“人民是谁”,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谁”。“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在中国历代领导人那里,“为人民”是一个构词要素和重要理念。比如,红军要“为人民打仗”,“为人民利益工作”,“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执政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等。为什么要“为人民”?因为党与人民之间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都需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人民共和国”一词最早也是出现在瓦窑堡会议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具备“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已经在人民解放区实现。新中国成立前后,围绕国号、国旗、国徽与宪法的政治进程及其最终样态,同样展现出强烈的人民性。

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部分),其中“人民”一词出现57次,超过此前7年频次之总和。中央档案馆藏。
因此,王绍光老师认为,除了新中国,世界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个政治体制,在其话语符号体系中“如此频繁地使用‘人民’一词,对人民的定位如此之高,对人民的承诺如此大张旗鼓、妇孺皆知”。“敢于作出这种承诺,就必须经受历史和人民检验,必须兑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作出这种承诺也是对共产党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响鼓重槌的鞭策,由此形成一个有效的象征性代表机制”。主题发言结束后,本场会议的三位与谈人分别作了评议。
刘晨光老师认为,王绍光老师的研究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内部,是对流俗“民主”观的纠正,有助于增进对“人民民主”概念的理解。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人民”面孔的二重性问题,它可以是已经建构完成的、意识形态化的“人民”,也可以是在革命过程中间不断创造、发现和建构的“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分化的当下,如何避免“人民”概念的空洞化、抽象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此,王涛老师指出,“人民”、“为人民”和“人民共和国”三大意符在今日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中至为重要,它们不是空洞的修辞,而是具体体现在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政策中。2020年以来,抗击新冠疫情与调控私人资本的政治举措不断展示着国家、政党的人民立场。与欧美诸国的抗疫表现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浪潮相比,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如同墨菲(比利时政治理论家、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所言,目前欧美政治已处在“民粹主义时刻”(populist moment)。而中国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植根于党的思想与国家的根基,这是克服新自由主义、资本消极作用的天然药方,能够形成对资本的节制。因此,维护和发扬其人民性对于国家治理与政党自身建设至关重要。同时,只有坚持和张扬人民的意符,才能保持自身的人民性或社会主义属性。
章永乐老师认为,刘晨光老师对“人民”概念空洞化的担忧与王涛老师提出的民粹主义问题或可一并看待,关键在于进一步分析“人民”意符的可能性。与中国革命话语中使用的“人民”概念不同,当代西方使用的“populism”一词具有模糊性,这是其力量来源,也是其天花板。这进一步凸显了激活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政治区分能力的重要性。随后他结合自身研究,从晚清、北洋时期的法律文本和国内外时势出发,完善了彼时“国民”、“人民”与“公民”概念的使用图谱。“国民”概念的推广离不开梁启超等人对国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理解,“人民”概念的出现必然涉及中共自身的理论基础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较之“国民”,“人民”可以是超地域的、国际主义的。“公民”概念最早出现在晚清,但民国的法律文本极少提及,大规模进入法律体系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针对三位与谈人的发言,王绍光老师作了简要回应。他首先谈到,自己对人民民主的理解是“四位一体”,象征性代表仅为其一。20世纪40年代之后,“人民”一词在西方政治学特别是主流民主理论中不断被消解,在中国却成为意符体系的核心与基础。在各类场合中不断出现的“人民”意符实际意味着一种承诺,一种暗含巨大压力以迫使相关机构与人员不断温习并兑现的承诺,值得警惕的恰恰是“人民”意符的淡化乃至消失。论及当下的西方民粹主义浪潮与各国“抗疫”表现,王绍光老师认为欧美政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大众代表性,“populism”不是人民运动,只是游离在几大党之间的情绪表达。新冠疫情如同一面放大镜,凸显了各国政治体制包括动员能力在内的政治能力差异,为未来三五年的各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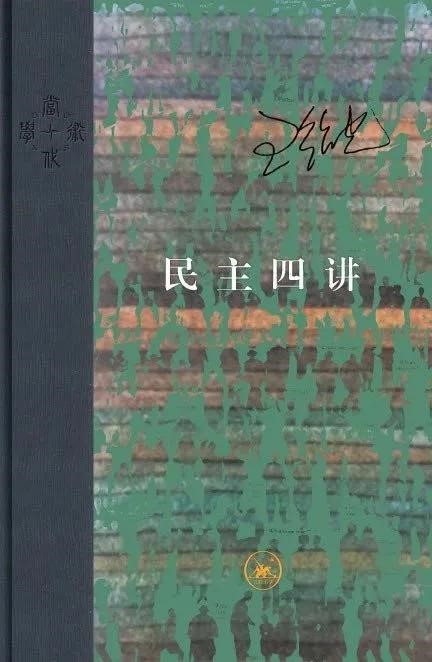
《民主四讲》,王绍光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